-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我国在“十四五”时期,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及无害化,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等,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目前我国推进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任务。实行垃圾分类与人民生存环境、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践行垃圾分类制度,为建设美丽中国、绿色中国添砖加瓦。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源消耗量大幅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总产出量持续加大。作为垃圾生产大国,我国垃圾治理起步较晚,在实际治理中仍存在很多缺陷。
基于此,本研究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重点回答了政府在城市垃圾分类中担负职能的内在逻辑,政府如何构建职能谱系,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升公共效益。“十四五”开局之际,明确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政府职能对于增进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
垃圾分类是垃圾污染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部分。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环境治理需企业、居民以及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但在城市垃圾分类实践中,相关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出现“搭便车”“机会主义”等外部性问题,垃圾治理任重道远。
就企业而言,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作为经济人,从成本利益角度考量,很难实现公共物品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市场机制对于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较低。现实中,企业进行垃圾分类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偏离。如,在垃圾分类收集环节,物流成本高、二次分拣消耗大,且缺乏统一的收集标准,规模效应难以形成,企业获利低。在垃圾焚烧处理环节,可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即可燃垃圾的析出,垃圾燃烧成本会提升,发电量产出会降低,显然与企业经济利益相背离[1]。
就居民而言,一方面,身为“理性经济人”的居民将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务自觉排除在责任范围之外,更不会主动增进公共利益。如,在垃圾投放环节,出于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考虑,大多数居民选择混合投放,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2]。另一方面,居民虽然希望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相关分类知识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思想认知不到位,且相应的监管机制不完善,仅凭个人自觉难以落实垃圾分类。
就社会组织而言,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参与者、环保意识理念的传播者、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监督者以及环境利益冲突的协调者在垃圾分类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社会组织极具公共价值追求,但很多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参与范围有限,专业人才较少,财力支持受阻,技术难题牵制,无法独自承担垃圾分类的重担。
综上,企业、居民、社会各主体均不具备单独处理垃圾分类问题的条件。正因如此,政府作为公共环境利益的代表,需要担负职能。
-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正在从倡导型向强制型转变。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3],提出了构建“无废城市”的规划,其中特别强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的重要性。2019年2月,住建部要求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底前基本建设完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基于此,各城市相继出台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规划。2019年7月,上海率先发布相关条例,迈入了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新时代。
实际上,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试点工作已推进20多年。2000年,我国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厦门、南京和桂林8大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4]。30年来,尽管国家层面多次力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显现出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存在很大问题:居民参与率和有效分类率仍然不高,分类处理技术投资率有待提升,社会组织支持力度有待加强等。
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市生活垃圾产出量急剧上升,由垃圾处理方式引发一系列生态安全和生命健康威胁。一方面,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出量空前激增。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以年均5%的速度激增。2018年我国城市固体垃圾产生量将近2.28亿t,与2000年相比增幅为93%。全国2/3城市陷于被垃圾包围的境地,1/4的城市缺乏合适的垃圾堆放场所[5]。“垃圾围城”已成为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一大弊病。但另一方面,垃圾末端处理方式不当加大了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健康的威胁。201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中51.9%为填埋,45.1%为焚烧[6]。填埋方式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是一种长期的生态隐患。焚烧则更会产生一氧化碳以及二噁英等有害物质。此外,许多垃圾处理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秩序以及社会稳定,如:2014年5月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引发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7];2018年筹划3年的湖北黄冈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还未开工即被迫暂停以及其他垃圾处理过程中带来的“邻避”事件。
垃圾分类治理严峻的客观形势表明,单纯依靠社会组织、居民等社会力量或者借助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垃圾治理问题,需要公共利益提供者的政府担负职能。
-
垃圾分类的政策效果和利益成果由各主体共享,才能实现可持续治理。因此,垃圾分类急需形成完整的规范化流程,既让垃圾应分尽分、应用尽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也使成本与收益在各个主体之间合理分配。
本研究将垃圾分类划定为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4个流程,各流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分类投放环节如果参与率低、准确率差,势必会影响处理环节的工作效率以及治污的成效。反之,如果处理环节设施不到位、技术水平低,也会打击投放环节个人的积极性。本研究基于这4个流程,构建垃圾分类中的政府职能谱系,进而研究政府在垃圾分类中应担负的主要职能。具体职能谱系,见图1。
图1可知,垃圾分类各流程中,每一流程都有对应的参与主体,履行相应的职责。针对每一流程政府应担负的职能进行总结,归纳为以下4大主要职能:制度设计职能、财政支持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和社会整合职能。其中,制度设计职能是前提,财政支持职能是保障,监督管理职能是基础,社会整合职能是核心。
-
所谓制度设计职能是在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作为制度供给方的政府应该具备的职能。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集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稀缺资源,合理的制度更是如此[8]。
在垃圾分类体系构建中,应该用权威可信的机制平衡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主体利益。2017年,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正式进入分类管制阶段。随后,深圳、南京等城市也相继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但是相关条例还有待健全。城市垃圾分类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健全城市垃圾治理的法规体系,制定配套的行政部门规章、完善各类相关标准规范。
-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要求政府推进,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完善责任延伸制度将产品责任从纳税人转移到生产者,将生产责任延伸到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流程,以引导生产者积极发挥资源再生作用[2]。此外,在垃圾处理环节中,垃圾处理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提高垃圾的燃值、控制垃圾处理成本,与控制污染理念相悖。因此,政府应制定明确的企业准入制度,规定每种类型垃圾的处理方式、处理标准和处理责任人。
-
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一项制度设计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取决于制度执行的交易成本[9],违反垃圾分类制度的交易成本过低是当前人们缺乏垃圾分类意识的主要诱因。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逻辑分析中指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关键之一在于依据贡献与否进行“选择性激励”,对于有悖于集体行动的人进行强制惩处[10]。基于此,政府应借助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培养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
-
垃圾分类是全过程管理,每一环节均要求政府发挥职能。为了防止在垃圾分类执行过程中出现部门相互推诿、互不担责的现象,政府应提前划分各个层级的职责,比如垃圾投放环节执行部门主要是街道、居委会和社区等,垃圾收集和运输环节执行部门主要是环卫部门,垃圾处理环节主要是市环保局以及环境质量监管局等。
-
所谓财政支持职能是指在垃圾分类中政府应承担的财政支出或者财政投资职能。城市垃圾分类中很多流程都需要大量费用支出,垃圾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持续性特点决定了政府需要担负财政支持职能,统筹各级部门补充资金、社会支持资金等,建立专项财政资金保障体系。
-
从垃圾分类全流程来看,社会成本包括生产和消费环节产生的垃圾污染成本,而现有的成本计算中只包含生产环节。且企业排污的成本远远小于企业治污的成本,急需进一步改革。从固体废弃物环境税层面来看,政府应该对以废弃物为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给予补贴,加大此类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企业增加相关资源利用的技术投入[11]。
-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尤其是环保产品易降解产品研发、机械化分类筛选、节能化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物质循环等方面需重点投入,促进技术转型升级。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提升物质利用的效率,控制垃圾处理污染程度。
-
从垃圾投放环节来看,需配备足量且专业的分类垃圾桶。从垃圾收集环节来看,垃圾收集密度较低,进行二次分拣的利润低,但其物流成本却较高[12]。而且废弃物形状大小千差万别,极不一致,很难形成规模效应。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难以负担,如果缺乏财政支持,收集环节阻力很大。从垃圾运输环节来看,不同类型的垃圾需要有不同型号、要求的环保运输车辆,各个社区的运输车辆汇总在一起便是很大的规模,需要政府财政支持。从垃圾处置环节来看,4类废弃物需精准送达处理系统。可回收垃圾送至废品回收利用系统,有害垃圾对接危险废物收运系统,厨余垃圾对应生物质的利用,其他垃圾主要以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每一类处理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政府财政补贴予以支持。
-
所谓监督管理职能是指政府在垃圾分类治理的执行监督、运营管理以及制度实施过程中应具备的职能。垃圾分类制度的良性运行,各项制度的切实落地,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均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机制,才能达到垃圾分类的预期目标。垃圾分类监管主体可以是个人、社会组织和大众媒体等,但是由于垃圾分类需兼具专业性、系统性、全面性,因此应由政府承担主要监管职能。
-
从垃圾投放环节来看,居民为生活垃圾投放环节的主体,在享受政府服务的同时应该履行相应的义务,但其义务的履行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可以委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辖区内的居民进行监管,按期对居民的垃圾投放状况进行核查,严格执行相应的奖惩制度。
-
垃圾收集运输和回收利用环节,政府大多外包给企业执行,而企业的“理性经济人”特性极易出现混收混运、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政府需引导企业借助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垃圾分类处理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定期核查,实现政府监管标准化。相关监督人员需依照制度规定记录其违规行为,并要求其进行整改。对于监督结果不仅要向上级部门反馈,还需要定期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开。
-
上级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下级职能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将检查结果作为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部分。此外,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的管理分支,负责理顺各个层级部门的职责,对整个垃圾分类全流程进行统筹监管。
-
所谓社会整合职能是指在垃圾分类治理中,政府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整合社会中其他分散的垃圾分类治理力量的职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明确以垃圾治理为重点,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活垃圾协同管理机制。为了发挥多方主体对垃圾分类的作用,要求政府构建一个主体广泛参与的生态环境决策平台。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引导实现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的均衡,从而使分散的利益偏好转化为整体的利益偏好。
-
从垃圾投放环节来看,政府部门应与街道、居委会对接,定期举办生活垃圾分类座谈会,向居民发放相关宣传册普及分类知识。还可以引入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垃圾分类自治模式,发挥公众主体意识参与社区自治。通过此类贴近居民的宣传、教育、自治等方式激发信任、社交等非正式激励要素发挥作用,从而使居民转变垃圾分类观念,自觉承担相应的责任。
-
从垃圾处理环节来看,政府可以引导企业成为实际运作的主体,借助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垃圾回收利用效率,控制污染效果。积极培育新品类废弃物的再生行业,对新兴再生行业提供政策和技术支持,待行业成熟后再交由市场自主运作。
-
发挥新闻媒体的媒介力量,一方面,通过宣传推广,更加及时、详细、准确的向社会发布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完善政府回应时间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媒体建立一个双向的信息公开程序,为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提供信息基础。
-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是新时代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居民切身利益,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本研究就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政府职能的内在逻辑和职能谱系分析。城市垃圾治理公共属性以及现实治理形势,构成政府在垃圾分类中担负职能的内在逻辑。基于垃圾分类流程,构建政府职能谱系,归纳出政府应担负的主要职能为:制度设计职能、财政支持职能、监督管理职能以及社会整合职能。其中,制度设计职能是前提,财政支持职能是保障,监督管理职能是基础,社会整合职能是核心。
垃圾分类治理涉及多个主体,居民、市场和社会均应肩负责任,积极投身于垃圾分类治理中,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治理局面。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政府职能
——内在逻辑及职能谱系Government functions in municipal solid waste classification: internal logic and function pedigree
-
摘要: 文章基于垃圾分类流程-主体-职能的分析框架,构建政府职能谱系。结果表明:政府应担负4大主要职能,制度设计职能是前提、财政支持职能是保障、监督管理职能是基础、社会整合职能是核心。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process-subject-func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pedigree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undertake four main functions. Among them, the system design is the premise, the financial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s the core.
-

-
[1] 杜春林, 黄涛珍.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J]. 行政论坛, 2019, 26(4): 116 − 121. doi: 10.3969/j.issn.1005-460X.2019.04.017 [2] 刘建军, 李小雨. 城市的风度: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与社区善治—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 27(1): 94 − 10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 (2019-01-21)[2021-03-0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1/21/content_5359620.htm. [4] 杜欢政, 刘飞仁.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难点及对策[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1(1): 134 − 144. [5] 钱小霞.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研究—基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19(10): 82 − 83. [6] 郭施宏, 陆健. 城市环境治理共治机制构建—以垃圾分类为例[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Z1): 132 − 141. [7] 孙壮珍.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4): 55 − 64. [8] 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M]. 杭行译, 韦森, 译审.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4: 28-30. [9] 范仓海. 中国转型期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9): 1 − 7.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1 [10]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7-9. [11] 陈思勤, 楼紫阳. 生活垃圾源头的分类减量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上海为例[J]. 上海城市管理, 2016, 25(1): 33 − 38. doi: 10.3969/j.issn.1674-7739.2016.01.009 [12] 杨雪锋, 王淼峰, 胡群. 垃圾分类: 行动困境、治理逻辑与政策路径[J]. 治理研究, 2019, 35(6): 108 − 114. doi: 10.3969/j.issn.1007-9092.2019.06.0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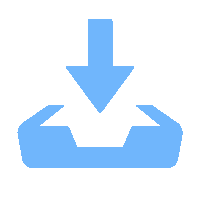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