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全球性灾难之一,酸雨被认为是当今最严重的一种跨境环境问题[1]。酸雨问题主要源于工业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生SO2)和汽车尾气的排放(产生NOx)[1],因此,人们治理酸雨的主要方法就是限制SO2和NOx等酸性污染物的产生。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酸雨问题就已经在美国出现,但直到1970年以前都未曾受到应有的关注,只是被用来反映空气质量状况的一项指标。随着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被首次报道,加之酸雨危机愈演愈烈,美国从联邦政府层面,开始了对酸雨治理模式的探索之路。
-
在当今酸雨治理领域中,命令—控制(Command-and-Control,CAC)和“市场调节”(Market-Based Instrument, MBI)是2种最具代表性的环境管制模式,美国完成由前者到后者的转型历经了二十余载。鉴于这2种模式在构成要素及运作机制等方面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在此,以酸雨治理实践为例,从实施主体、动力来源和运行机制3个方面,首先对2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加以阐释。
-
酸雨治理模式的实施主体,是指对酸雨进行治理的行为主体,它承担着酸雨治理的责任,并被赋予实施治理的相应权力。实施主体对酸雨治理的主观认知和态度,及对酸雨进行治理的能力,都会对酸雨治理的客观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命令—控制模式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国家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3个组成部分),它们借助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法定的权力和权威,以发布酸雨管制命令、制定酸雨防治法规、设定SO2排放标准、开展对排污单位的监督审查等方式,实施对酸雨的治理。
市场调节模式则通过将酸雨治理的环境成本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相挂钩的方式,将酸雨治理的行为主体由国家机构转向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企业会自发地依据其自身经营的成本和收益状况,灵活地做出“污染多少,治理多少”的选择,而不必受制于环境监管者设定的酸雨管制模式。
-
酸雨治理模式的动力来源,是指推动酸雨治理模式得以实施的主要动因和激励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酸雨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
命令—控制模式的动力来源,是在世界环保运动蓬勃兴起与美国国内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国家机构对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环境保护事业所必须担负的责任、义务和职能。
市场调节模式的动力来源,则是市场运行中成本—收益衡量下的经济效益。在市场调节模式中,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借助一些经济激励措施,将企业治理酸雨的费用内化到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当中。为了花费最少的治污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企业便会想方设法地减少污染排放。因此,较之命令—控制模式,市场调节模式在酸雨治理的过程中会呈现出更加灵活、自觉的特点。
-
酸雨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是指推动酸雨治理模式运行并发挥作用的逻辑、程序、方式与路径,它随酸雨治理模式中其他要素所产生的变化而变化,直接决定了某一酸雨治理模式的具体表现形态。
命令—控制模式依靠国家机构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以外部约束的方式对致使酸雨产生的排污企业实施最直接的管控。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机构首先需要通过立法手段界定法律所允许的SO2等酸性污染物的最大排放量,然后再借助行政手段对那些超过最大排放量的行为施以惩罚。由于该模式的运行建立在各种严格的酸雨管制标准和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基础之上,因此实施主体对于各企业排污信息的掌握尤为重要。
市场调节模式则主要依靠经济和市场手段,以内在约束的方式对致使酸雨产生的排污企业实施间接性管控。为了充分调动企业治理酸雨的积极性,在制定总体的SO2减排目标后,环境监管者会借助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以经济诱导环保的方式将企业治理酸雨的责任与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结合起来,以此来促使其自发地采取一些酸雨治理措施。由于该模式的运行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因此合理恰当的经济激励措施是其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
-
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美国酸雨治理的“无政府时代”。彼时,以联邦政府为主的国家机构对于国内酸雨乃至空气污染问题并未施加过多的干预。而后,随着酸雨等跨境污染问题愈发严峻,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画地为牢”式治理方式,以及民间环保运动的“分散性”弊端日显。美国最终于1970年伴随《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实施确立了以国家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命令—控制模式,并由此开启了借助行政、立法和司法手段共同管制空气污染的“命令—控制”时期。
-
“命令—控制”时期美国治理酸雨的主体是以美国联邦政府为主的国家机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还包括以国会为代表的立法机构和以联邦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构。
在国家机构的三方实施主体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1970年,尼克松政府开启了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就每年所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向国会提交咨文的先例[2],还特别成立了以美国环保局为代表的专门性环境管制机构。自此,“环境保护不再仅仅是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承担起对环境保护的主要领导责任”[3]。国会作为各方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场所,也在此期间表现出强烈的环保价值取向。一般而言,在参众两院表决时,民主党人支持环保的热情要远高于共和党人。在民主党人掌控着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70年代,国会先后于1970和1977年2次修订《清洁空气法》。联邦法院虽然没有像上述主体的态度倾向那样明显,但在总统和国会这两大利益主体的共同影响下,其作为宪政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在不损害宪法效力的情况下也是会考虑到维护联邦政府和国会的权威,从而向环保势力一方倾斜的。
由此可见,在美国治理酸雨的命令—控制模式中,尽管作为共同实施主体的三大部门行使权力的领域各不相同,但其在此时期内支持美国酸雨治理的态度却是基本趋于一致的。
-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酸雨问题的全面爆发时期,也是命令—控制模式的高度发展时期,其发展的主要动因在于国家机构承担环保责任的需要。
从1970年1月1日《国家环境政策法》正式生效的那一刻起,美国进入到了“环境保护的十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家机构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还是在出台环保政策的数量和水平上,都较之前有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酸雨现象在70年代初期愈发严峻,甚至已损害到美国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安全。在此影响下,特别是在热衷于环保的民主党人占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70年代,作为“最具有政治责任感的联邦机构”[4],国会和各州议会首先应承担起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重大使命——通过环境立法的方式对酸雨问题实施管控。
鉴于酸雨问题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一方面,它涉及美国与邻国加拿大之间在共同应对跨境空气污染问题时进行的合作与博弈;另一方面,在国内环保运动高涨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联邦政府也需要向公众对其所必须承担的环保责任作出积极回应,以求弥补在经济问题上损伤的政治权威。特别是酸雨本就是一个跨境性质的空气污染问题,污染程度的加深使得各州与地区之间各自治污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在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只会使污染者的“搭便车”行为愈演愈烈。因此,无论是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还是出于国家机构所必须担负的环保责任的考量,都迫切需要联邦从国家政治层面对酸雨问题加以协调和管制。
-
命令—控制模式的运行围绕国家立法领域的措施展开,配合行政和司法手段的干预,三者共同开创了美国以国家强制力方式来解决酸雨问题的先河。
首先,从国家立法层面来看。命令—控制时期是联邦以立法手段应对酸雨问题的开端,这为日后美国“酸雨计划”的正式出台奠定了充实的法理依据。在《197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中,法案授权美国环保局对于6种危害公众健康与福利的空气污染物质设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AAQS)”[5],其中就包括致使酸雨产生的SO2和NOx。在《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中,法案对于酸雨问题的管控更加具体。在第123条条款中,法案增加了限制高烟囱的使用,使之不能经常作为一项污染控制技术的决定[6];在第110和第126条条款中,法案首次就各州酸性污染物的跨州际传播及相关申诉问题进行了界定[6];在第115条条款中,法案则对国家解决酸性污染物跨境传播的程序问题作出了说明[6]。
其次,从行政措施层面来看。联邦政府在此期间发布的酸雨管制命令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根据1970年法案的要求制定SO2和NOx等酸性污染物的排放标准[7],见表1。
1971年4月,美国环保局分别将SO2和NOx的“国家一级空气质量标准”的年度算数平均值设为80和100 μg/m3[8]。自此,美国的酸雨管控工作有了科学的依据和准则。第二,为了使更多地区尽快达到NAAQS的要求,美国环保局采纳了通过建造高烟囱的方式来将SO2等酸性污染物排放到高空中,以此来稀释和分散地表污染物浓度的高烟囱政策。据悉,1960年,美国烟囱的平均高度约74 m;1970年,已经存在2个高度超过152 m的烟囱;到了1980年,烟囱的平均高度已达到223 m[9]。第三,开始就跨境酸雨防治问题与加拿大政府展开合作。1978年,两国建立了“空气污染物远距离传输双边研究磋商小组”,开始对酸雨问题展开科学研究[10]。到了1979年,两国又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酸雨在北美地区的起因、传播和影响等内容的科学报告[11],同时还签署了《跨界空气质量联合声明》,表达了美加双方想要“共同减少或防止损害公众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跨界空气污染问题的决心”[10]。
最后,从司法诉讼层面来看。美国联邦法院支持为酸雨治理申诉的态度主张也在此期间表现得愈发明显,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73年“西宾夕法尼亚电力公司诉特雷恩案”[12]。西宾夕法尼亚电力公司是一家主要排放含硫化合物的电力企业。1973年,它因不满所在州向美国环保局提交的州实施计划(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SIP)中对于SO2等酸性污染物设定了高于NAAQS的做法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最高法院以凡是符合1970年法案要求的SIP均可被执行为由驳回了电力公司因过高的经济技术成本而想要执行另外一种“不那么严格”的排污标准的主张[12]。此外,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诉环保局案”“美国大河电力公司诉环保局案”“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诉特雷恩案”等案件中,联邦法院同样对于工业企业试图通过建造高烟囱以规避NAAQS的做法进行了“抵制”[9]。
-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受滞胀危机的持续影响,全国对于不计成本治理污染的命令—控制模式的信心开始动摇。但鉴于酸雨危机的不断恶化乃至国际化,又使得美国无法完全放弃对酸雨的治理,因而从这时开始,酸雨治理模式中逐渐孕育出一些市场因素。这些市场因素在大力倡导“反环保、促发展”的里根政府时期逐渐完善和发展,最终,随着《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第四章“酸雨计划”(Acid Rain Program)的出台,美国正式确立了酸雨治理的市场调节模式。与命令—控制模式不同,在该模式中,市场机制逐渐开始取代联邦管控的统治地位,在酸雨乃至空气污染治理领域中日渐发挥起主导性作用。
-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美国在1990年之后进行酸雨治理的主体,主要就是受到国家“酸雨计划”管制的各类排放SO2和NOx等酸性污染物的工业企业。但是,鉴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排污企业密切相关的一些诸如美国联邦政府、工商业投机者以及环保主义者等“非污染物排放主体”也积极参与其中。
首先来说市场调节模式中最重要的实施主体——排污企业。通常而言,主动参与到酸雨治理过程中的排污企业有2种:一种是在“酸雨计划”中被明确列出的法定执行者,包括被列入“酸雨计划”第一阶段管控范围的位于美国东部和中西部21个州的110家发电厂的263个污染源,和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增加的2 000多家生产规模大于2.5万KW的SO2排放企业[13],它们是导致美国SO2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力量;另一种则是通过“选择—加入计划(Opt-in program)”参与其中的自愿加入者,包括一些生产规模小于2.5万千瓦的发电设备、工业锅炉以及未被列入“酸雨计划”的城市废物焚烧炉等污染源[14]。由于它们自主降低1 t的SO2排放的成本通常会低于排污交易市场中1 t的SO2排放配额的平均售价,因此加入“酸雨计划”的SO2排污交易机制中能够使其“有利可图”。
此外,市场调节模式还有3种“非污染物排放主体”。其一是以美国环保局为代表的政府监管者,他们主要通过监督和审查的方式对市场调节模式辅之以必要的行政管控措施。其二是工商业投机者,他们通过将SO2排放配额视作一种投机产品,以“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方式活跃着SO2排污交易市场。其三是环保主义者,他们购买SO2排放配额的主要目的是将其储蓄不再卖出,以此来减少排污配额在交易市场中的流通总量,从而达到控制社会中SO2总体排放量的目的。当然,除了环保主义者之外,政府有时也会扮演这一角色。
-
1990年“酸雨计划”的出台是美国市场调节模式取代命令—控制模式的最终胜利,该模式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主要驱动力在于各排污企业对经济效益的不断追求。
早在“酸雨计划”出台前的数十年间,国会便已经开始就如何处理SO2排放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截至1989年(即“酸雨计划”正式出台的前一年),国会已然对酸雨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大大小小共计70多个议案[15],这些议案所反映出的共同主旨在于,在最大限度节省治污成本的基础上寻找到解决酸雨问题的新路径。由于滞胀危机余波的影响,国家机构和排污企业在此期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的市场手段上。随后,在各方势力就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来节省酸雨治理成本、提高酸雨治理效率等问题展开了数轮博弈与交锋后,最终得以兼顾企业和环保主义者利益的、既清洁又廉价的“酸雨计划”应运而生。
不同于命令—控制模式中不计成本的强制性污染管控模式,经济发展的诉求在“酸雨计划”的运行过程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一方面,这是出于对20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需要快速恢复和发展的现实需要的考虑;另一方面,唯有将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引入污染治理领域,换言之,唯有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才更能引导企业自觉地在最大程度上、且最持久地对空气污染问题作出改善。而从后续“酸雨计划”的实施过程来看,这的确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控制模式所不能及的。
在市场调节模式的实施下,借助于排污配额的交易过程,美国不仅成功建立了世界上首个SO2排污权交易市场,还通过允许合理买卖SO2排放权利的方式为企业常常会选择“搭便车”的污染治理责任赋予了经济价值。其实,无论是在“酸雨计划”出台之前的讨论设计阶段,还是在市场调节模式的正式运行阶段,以企业经济效益为重的理念贯穿于“酸雨计划”的运行始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仅是政策制定者引导排污企业自觉参与到酸雨治理进程中的一座桥梁,更是在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下保障排污权交易过程得以正常运转的最大动力。
-
以“酸雨计划”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含以下4个方面。
-
这一机制具有2层含义:首先,对致使酸雨产生的SO2和NOx等酸性污染物设定明确的总量上限。《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在第四章开篇中明确表示:“为减少酸沉积带来的不利影响,预将国家本土48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SO2年排放总量在1980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1 000万t,将NOx的排放量在1980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200万t”[16]。随后,国会还将达成总量上限目标的具体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分别设定更具体的排污上限。其次,在实现总量上限目标的方式选择上,“酸雨计划”给了各排污单位足够的灵活性。换句话说,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总量上限目标的前提下,各排污单位可根据其自身的运营情况选择“最能使其效益最大化”的污染治理方式。此外,“酸雨计划”还鼓励各排污单位通过自主研发或引进治污新技术的方式来实现SO2排放总量的减少。
-
排污配额(allowance),即美国环保局授予各排污单位排放定额SO2的权利[16]。在“酸雨计划”中,各排污单位获得SO2排放配额的方式主要有3种:无偿获取、有偿交易和技术奖励。其中,无偿获取方式是三者中最主要且最稳定的一种配额分配来源,大约占初始分配配额总量的97.2%[17]。按照1990年法案规定,美国环保局局长需对所有被管制的排污单位分配为期1年的排污配额,且配额分配的数量应等于法案允许的SO2最高排放上限[16]。除了无偿获取,各排污单位还可通过有偿交易的方式购买到一定数量的排污配额。根据法案要求,美国环保局会从“酸雨计划”第一、二阶段无偿发放的排污配额总量中各扣除2.8%的数额,用于建立一个“特定配额储备”,以供排污配额的有偿出售[16]。通常情况下,美国环保局出售排污配额的方式主要有2种:直接出售和拍卖出售。此外,各排污单位还可通过更新现有排污技术设备的方式来获取额外的“奖励性配额”。
-
这是整个“酸雨计划”中最核心的环节。根据“排污配额可在各排污单位和任意配额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易和转让”[16]的要求,美国建立了世界上首个SO2排污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各排污单位可对其削减1 t的SO2的成本与市场中一单位排污配额的售价进行比较,以此来自行决定其实现SO2总量上限目标的方式。当然,对于本年度没有抵消完SO2实际排放量的剩余配额,可转入下一年使用;对于“酸雨计划”第一阶段内没有使用完的排污配额,可转入第二阶段使用;但是不可在配额未正式发放前就“预使用”排污配额[16]。
-
这一机制包含以下3个子系统:排污跟踪系统、配额跟踪系统和年度调整系统。排污跟踪系统是监督审查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依靠在各污染源上安装和运行对于SO2的“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来实现[16]。通常情况下,各排污单位至少要以1个季度为期限,定期将其监测到的SO2排放数据向美国环保局如实汇报,以此来确保美国环保局在执行“酸雨计划”其他各运行机制时所需要的可靠数据来源。配额跟踪系统是美国环保局为掌握其自身及各排污单位的配额持有情况而建立的一种计算机控制系统,也是查阅配额分配、交易、年终审查等官方记录的唯一途径。最后,在对于排污单位的年度SO2排放总量和年度排污配额持有量等信息都准确掌握之后,美国环保局便会通过年度调整系统核算出这一年各排污单位应被扣除的排污配额总量。当然,对于最终年度排污配额持有量不足以抵消其年度SO2排放总量的排污单位,美国环保局要对其超额排放SO2的行为施以严厉的行政和经济处罚。
-
在经济至上的发展观和功利主义自然观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领域曾走上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式的发展道路。在70年代生态危机空前加剧的背景下,尽管美国一度确立了以国家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命令—控制模式,但随着滞胀危机的爆发及国内经济形势的下滑,很快又出现了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置于环境保护之上的倾向。虽然经过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复博弈,致力于平衡经济与环境效益的“酸雨计划”最终产生,但还是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将美国“酸雨计划”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经济与环境平衡发展的理念,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相融合,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
美国酸雨治理模式的转型历经了从“依靠市场力量—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重新重视市场力量”这一“失灵”与“回归”相交错的探索路径。1990年“酸雨计划”出台后,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层面的SO2排污交易市场,较之改革路径上最初依靠的“单一型市场”而言,这个新型市场的建立与其说是再次依靠市场力量,不如说是有政府的干预为其保驾护航。这也是90年代以前美国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力量为何会频繁出现“失灵”的原因,这种“回归”实则是对命令—控制模式进一步市场化的结果。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单一型污染治理模式都并非完美无瑕,在进一步深化我国环境管制模式的市场化改革之际,我们一定要从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力量的一元论思维中解脱出来,本着“管制为先,市场并重”的原则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以此来制定出更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管制模式。
-
酸雨、温室气体排放等跨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是某一国的个体行为,还是一种国际行为,需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美加酸雨谈判始于1977年,直至1991年双方才最终签署美加《空气质量协定》(Air Quality Agreement)。在此15年间,即便是在双方政府曾就共同治理酸雨的问题多次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还是有协议因美方政府的单方面否认而夭折。这是霸权主义国家以牺牲他国环境为代价维护本国利益的惯用手段,我们不但不应效仿还应对其予以谴责和抵制。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与引领者,我们要摒弃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加强与邻国及世界其他各国在国际环保事务中的多边化、区域化与全球化合作,努力提升本国对国际环保事业的自主贡献率,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中国力量,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充分彰显大国担当。
-
美国酸雨治理模式变迁既有《197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授权同意将酸雨治理的主导权收归联邦政府作为法律保障,同时也与美国数百年形成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但在此之前,美国曾耗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去确立联邦政府管制环境进而解决酸雨危机的合法性。如此,不仅可以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环境管制又回到70年代以前的“州权时代”,还能够防止日后这些酸雨管控条例成为一纸空文。对比美国这一环境治理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发挥中央政府治理环境的主导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鉴于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发展得并不完善。为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治污模式的市场化改革双项并举的时代,我国应从国情出发,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市场力量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杠杆性作用,同时进一步健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环境法律体系,以使我国的环境治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从“命令—控制”到“市场调节”的环境管制模式研究及启示
——以美国酸雨治理为例Research and enlight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odel from “command-and-control” to “market-based instrument”
-
摘要: 美国酸雨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在美国乃至世界环境与经济史上均具有典型意义。随着1990年“酸雨计划”的出台,美国完成了酸雨治理由“命令—控制”向“市场调节”模式的转变,也为世界各国在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历史“范式”。在对美国酸雨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阶段性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2种典型的环境管制模式的主要特征入手,阐释“命令—控制”模式最终被“市场调节”模式所取代的必然性,对于研究我国环境管制模式的转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Abstract: The transition of the acid rain regulation model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typical significance both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he world.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Acid Rain Program” in 1990, the United States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of acid rain regulation from a “command-and-control” model to a “market-based instrument” model and provided a historical “paradigm”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transition of acid rain regulation mod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alyzed from a phased historical poin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wo typi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odels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command-control” model being replaced by the “market-based instrument” model was explained.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transi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odels in our country.
-

-
表 1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Table 1.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污染物 国家一级环境质量标准 国家二级环境质量标准 均值类型 标准浓度水平 均值类型 标准浓度水平 一氧化碳 8小时 10 mg·m−3 未设定 无 1小时 40 mg·m−3 未设定 无 铅 平均每季最大值 1.5 μg·m−3 平均每季最大值 1.5 μg·m−3 氮氧化物 每年算数平均值 100 μg·m−3 每年算数平均值 100 μg·m−3 臭氧 每天1小时平均最大值 235 μg·m−3 每天1小时平均最大值 235 μg·m−3 颗粒物(PM10) 每年算数平均值 50 μg·m−3 每年算数平均值 50 μg·m−3 24小时 150 μg·m−3 24小时 150 μg·m−3 二氧化硫 每年算数平均值 80 μg·m−3 3小时 1300 μg·m−3 24小时 365 μg·m−3 -
[1] SINGH A, AGRAWAL M. Acid rain and its ecological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2008, 29(1): 15 − 24. [2] FLIPPEN J B. Nixon and the environment[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00. [3] REITZE A. Air pollution control law: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M]. Washington D. C. : 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2001. [4] PIERCE R J.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federalism, and administrative law: agency power to preempt state regulation[J].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1985, 46(607): 607 − 671. [5]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ublic Law 91-604(1970)[A].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ting Office, 1970. [6]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ublic Law 95-95(1977)[A].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ting Office, 1980. [7] PORTNEY P R, STAVINS R N. Public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M]. Washington D. C. :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2000. [8]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Federal Register. [EB]. Federal Register, 1973, 38(178): 25679-1984. [9] VESTIGO J R. Acid rain and tall stack regulation under the Clean Air Act[J]. Environmental Law, 1985, 15(4): 711 − 744. [10] SULLIVAN J L. Beyond the bargaining table: Canada's use of section 115 of the United States Clean Air Act to prevent acid rain[J].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83, 16(193): 193 − 227. [11] CUTLER A C, ZACHER M W.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2. [12]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West Penn Power Co. v. Train, 538 F. 2d 1020[R]. Washington D. C. : District of Third Circuit, 1976. [13]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cid rain program, SO2 reduction[EB/OL]. [2021-12-01]. https://www.epa.gov/acidrain/acid-rain-program/. [14]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he opt-in program: overview for combustion sources[EB/OL]. [2021-12-01]. https://nepis.epa.gov/Exe/ZyPURL.cgi?Dockey=00000M2K.txt.pdf. [15] MCLEAN B J. Evolution of marketable permits: the US experience with sulfur dioxide allowance trading[J]. Int. J.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1997, 8(1/2): 19 − 36. [16] United States Congress. Public Law 101-549(1990)[A].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ting Office, 1993. [17] 李晓绩. 排污权交易制度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0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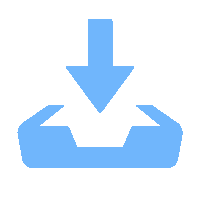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